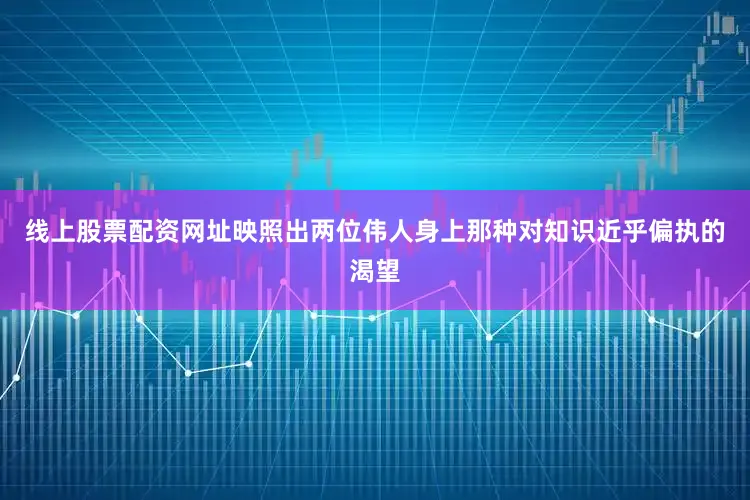
三天不学,赶不上刘少奇。一天不用功,赶不上毛泽东。这两句话,藏着多少故事?

这不只是一句简单的相互赞誉,更像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两位伟人身上那种对知识近乎偏执的渴望。这种渴望,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需要,或者改造世界的宏大目标使然,它似乎更深植于他们的骨血之中,是一种面对未知世界时本能的好奇与敬畏。
想当年,刘少奇还是个孩子时,就得了“刘九书柜”的雅号。这雅号可不是谁强加的,完全是他自己钻进书堆里得来的。从家里的旧书,到表哥带回来的《辛亥革命始末记》,每一页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。试想一下,一个乡间少年,读着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始末,心里会是怎样的波澜壮阔?
为了看书,他能有多拼?上半夜借着邻居磨坊里透出的一点点微光,下半夜就着母亲特意多添了半勺油的灯火,伏案夜读。这种劲头,早已超出了老师布置作业的范畴,更像是一种“不搞明白誓不罢休”的较真儿,一种内在的求知饥渴。

这份较真儿伴随了他一生。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,语言不通,环境陌生,用萧劲光将军的话说,他“几乎没有个人爱好”,把所有精力都扎进了学习俄文和《共产党宣言》里。这哪里是单纯完成任务,分明是在饥饿地汲取思想的养分,寻找能改造中国的武器。
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,在腥风血雨的敌后根据地,死亡随时可能降临。张爱萍将军深夜去看他,看到他竟然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书,书上圈圈点点,密密麻麻。还有那穿越上百道封锁线的漫长转移路途,他硬是系统地研读了中国历史和哲学史。这需要的,已经不是简单的毅力,而是把学习真正变成了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需要。
毛主席呢?他读书的广度和深度,同样让人叹为观止。从经史子集到西方哲学、自然科学,无所不包。他说过一句狠话:“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,那么就要学习9年359天方才罢休。”这不是空话,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手里依然捧着书,是明代的《容斋随笔》。
这种对学习的极致执着,除了改变中国的雄心,是不是也源于一种深刻的“本领恐慌”?他太清楚,革命队伍里有的是凭着一股子热血,却对复杂问题缺乏深刻认识的“半瓶子醋”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如此曲折艰难,仅靠经验和口号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他反复强调要“挤”时间、“钻”进去学,无论老少,不分文化程度。

更有意思的是,他们不仅自己是学霸,还都是研究如何学习和如何应用的专家。刘少奇同志尤其看重理论联系实际。他后来反思早期革命的挫折,认为很大程度上是“理论上的失败”,批评有些人抱着洋本本,却对中国国情视而不见,或者学了理论却不会用。
想想他领导安源罢工的经历,一开始对煤矿和工人一窍不通,但他没有拍脑袋,而是连夜向工人请教,跟群众深入交流,把情况摸了个门儿清,这才制定策略。他常说,学理论就像学游泳学骑车,光看说明书没用,得跳下水去扑腾,摔几跤才能学会。真知不是在书本里长出来的,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。
毛主席最后一次见刘少奇时,推荐的那三本书:《淮南子》、狄德罗和海格尔的著作,也极富深意。在那样的时刻,推荐这几本看似不相干的书,或许是在传递一种复杂的信息。《淮南子》博杂包容,兼采各家,或许是希望他能从更开阔的视野看问题,体悟黄老哲学中那些变通与包容的智慧。而狄德罗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海格尔的辩证法,可能是在提示要用发展的、联系的眼光看世界,避免思想上的僵化和固步自封。这三本书,就像三把隐喻的钥匙,毛主席也许是希望老战友能用它们打开新的思考空间,保持思想的活力。可惜,王光美同志后来回忆说,刘少奇未能找到那两本外国著作。
“三天不学习,赶不上刘少奇”。“一天不用功,赶不上毛泽东”。今天再看这两句话,它们已超越了字面上的谦逊与赞美,成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一种精神写照。他们用行动告诉世界,带领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,靠的不是侥幸和冲动,而是建立在对知识的极端渴求和活学活用之上。

他们深知,革命成功只是第一步,进城管理国家,面临的挑战远比打仗复杂得多。如果停止学习,抱残守缺,就可能在新问题面前一败涂地,甚至埋下“内部发生的危险”。他们的学习,是为了解决问题,为了建设未来。毛主席从《三国演义》里看军事权谋和哲学,刘少奇在报告里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,都是这种“学习为了使用”的最好证明。
重温这段“学习史”,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伟人的风范,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召唤。在信息爆炸、知识飞速迭代的今天,那种把学习当成本能、把理论融入实践的精神,对于我们每个人,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。学习不止,探索不息,这或许是他们留给这个时代的,最宝贵的遗产之一。
金领速配-河南股指配资-咸阳股票配资-开户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