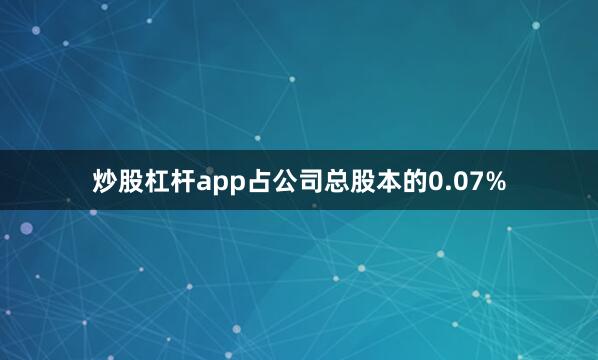一
明万历三十五年(1607 年),北京宣武门内的天主堂里,45 岁的徐光启正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俯身案前,用毛笔在宣纸上勾勒几何图形。
此时的中国,科举士人沉迷 "八股",天文历法仍沿用元代《授时历》,误差已达 "节气差一日";
而西方经过文艺复兴,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的逻辑体系已趋完善。
身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徐光启,却敏锐意识到 "格物致知" 需借西方科学,这场看似普通的翻译,实则开启了中国科学史上 "中西对话" 的先河。
二
据《徐光启集・几何原本序》记载,徐光启初识利玛窦时,便被西方 "度数之学"(数学)吸引,力邀翻译《几何原本》。
但翻译过程困难重重:西方 "点、线、面" 的抽象概念无对应中文词汇,逻辑推理方式与传统 "悟道明心" 截然不同。
利玛窦曾因 "译文晦涩,士人难明" 欲半途而废,徐光启却坚持:"此书穷理正确,虽难,然为万世利,必成之。"
展开剩余78%最关键的突破是对 "Geometry" 的翻译。
利玛窦主张音译为 "奇器",徐光启却据《墨子・经上》"圜,一中同长也" 的几何思想,创 "几何" 一词,既含 "测量之术" 意,又暗合 "穷究数理" 义。
他在译到 "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" 时,特意加入 "以勾股验之" 的注解,用中国传统算学验证西方定理。
据《明史・徐光启传》补充,某夜译至 "平行线永不相交",徐光启为让士人理解,取两根竹筷平行放置,笑道:"此如两人同行,虽万里而终不相遇。"
这种 "中西互释" 的方法,让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终成,刊行后 "士人争相传阅,虽老儒亦习之"。
三
《徐光启集・几何原本杂议》原文
"此书有四不必:不必疑,不必揣,不必试,不必改。有四不可得:欲脱之不可得,欲驳之不可得,欲减之不可得,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。" 这段话既赞西方逻辑的严谨,也暗含对传统治学 "臆断" 的反思。
《明史・徐光启传》补充细节
"光启从利玛窦学天文、历算、火器,尽其术。与利玛窦共译《几何原本》,其书穷理正确,为中国未有。光启言:' 欲求超胜,必先会通;会通之前,必先翻译。' 译书时,每字每句必反复推敲,三年乃成前六卷。"
两段文献相互印证,既展现了翻译的艰辛,也凸显了徐光启 "会通中西" 的远见。
四
徐光启虽为科举出身,却反感 "空谈义理",主张 "学问必有事功"。
他将《几何原本》视为 "经世之具",在序言中说:"农、工、兵、医,皆需度数,此书乃万学之基。"
这种 "实学" 思想,与明末顾炎武 "经世致用" 相呼应,推动儒学从 "心性之学" 向 "实用之学" 拓展。
他不盲目排斥西学,也不放弃中学根基。
翻译时既保留 "点、线、角" 等新术语,又用《九章算术》的 "勾股" 解释西方定理;
既推崇欧几里得的 "演绎逻辑",又强调 "验之于物" 的实证精神。
这种 "取其精华,补我不足" 的态度,打破了 "华夏中心论" 的局限,展现了文化自信的开放形态。
作为翰林院官员,徐光启利用职务推动西学传播。
向万历帝进呈《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》,主张用西方天文仪器改历;
编写《农政全书》时引入西方水利技术。
他的努力证明,即便在僵化的科举体制中,仍可开辟科学发展的缝隙,体现了传统士人的担当与创新。
五
清代康熙皇帝研习《几何原本》,命梅文鼎等编纂《数理精蕴》,将西方数学纳入官方学术;
清末李善兰完成《几何原本》后九卷翻译,梁启超称 "此书开启中国科学之门,光启功不可没"。
徐光启创造的 "几何"" 点 ""线"" 平行线 " 等术语沿用至今,成为中文科学词汇的基础;
其 "信、达、雅" 的翻译原则(虽未明言,实则践行),影响了严复译《天演论》等后世译作。
上海徐家汇(因徐光启墓地得名)成为近代西学传播中心,交通大学前身 "南洋公学" 便源于此;
2003 年,"徐光启与《几何原本》" 邮票发行,象征其 "会通中西" 的精神在当代的延续。
发布于:广东省金领速配-河南股指配资-咸阳股票配资-开户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